政治课(6图)
发布时间:2011-02-23 10:37 | 来源:中国青年报 2011年02月16日 第12版 | 查看:1475次

董丰均在办公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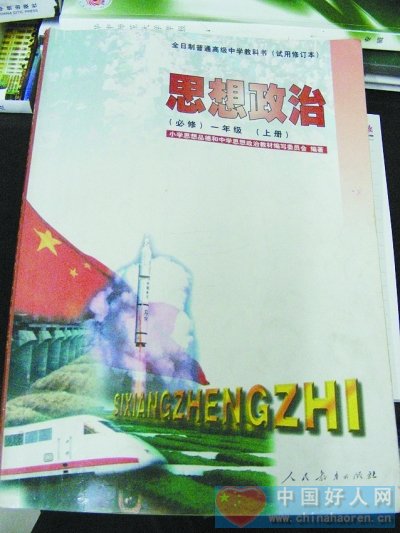
中学政治课本

董丰均当年收到的张道旭的信

董丰均在马基雅维利墓前

董丰均的书籍和发表文章的刊物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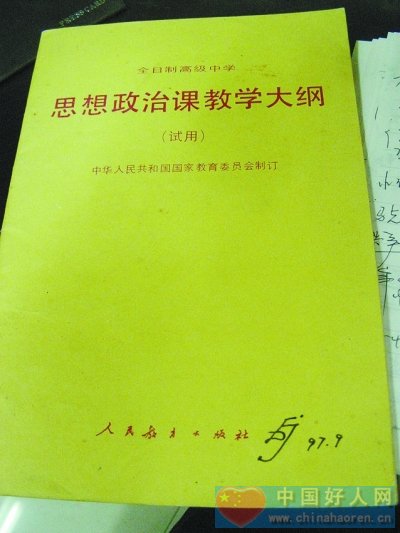
董丰均用过的教学大纲
告别中学讲台已近两年,但59岁的董丰均始终觉得自己在政治教学上的“最后一课”,至今还没上完。
这一课的内容,是要纠正中学本中他认为有待商榷的一些表述。为了补好这一课,他的办公桌上,长年备着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、《资本论》、凯恩斯的《货币论》,以及多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中学政治教材等书籍。身后的报架上,夹着他爱看的几份报纸,倚着书柜堆放的旧报纸,高过了他的头顶。
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这位政治老师眼里,这些书报,都牵扯着他未竟的政治课教学。从2009年秋天至今,他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这些书报间,寻找答案。
一封信带来的改变
困扰董丰均的问题,出现在2003年10月22日。
那天,他拆开了一封写着“董丰均校长收”的信,随后这个教了27年政治课的老师便开始“寝食难安”。
写信人是十堰市房县一中政治教师张道旭。那年暑假,他参加了全市高中政治教师暑期培训,主讲老师就是十堰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董丰均。
刚教了3年政治的年轻人在《思想政治课教学》杂志上看到,有人在《纸币的职能》一文中的观点,与高一政治课本上的提法互相矛盾。
“我有疑问,便给董老师写信请教。”张道旭回忆说。郧阳中学是十堰市最好的中学之一,董丰均时任副校长。
此前,董丰均教过的高三学生中有多人的高考政治成绩列鄂西北地区第一。在张道旭眼里,董是整个十堰市最优秀的政治老师,应该可以解答自己的疑问。
信中,执弟子礼的张道旭问道:“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、贮藏手段、世界货币的职能?”
课本的标准答案很明确:没有。但这一次,董丰均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回答,而是把自己手里的政治课本又仔细翻阅了5遍。他发现,书里说纸币没有价值尺度、贮藏手段、世界货币的职能,但隔了没几页,又说美元、英镑、日元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。
“这不是前后矛盾吗?”他摊开双手,用手指敲着办公桌厉声道。
董丰均一直颇为自豪的一点是,自己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被学生的问题难倒过。但这一天,他发现自己第一次被“问住了”。尽管有些难以接受,但他还是承认了这一现实。在给张道旭回信中他说:“这个问题容我研究后,再给你答复。”
在女儿董蕾的记忆里,爸爸喜欢跟人争辩,并且很少有争输的时候。因为他做什么事情,都喜欢从理论上搞清楚。然而这一次,自认为说服能力比较强的董丰均发现,自己教了20多年书,这些理论却依然没搞清楚。他打心底里难以接受。
更何况在他看来,张道旭是执弟子礼郑重提出这个问题的,学生问老师问题,老师不能不闻不答,而且必须给出负责任的明确答复,这是老师的职业道德要求。
不问对错的27年
如何答复这个问题,从此成了董丰均的心病。他开始四处寻找答案。
他从家里的地下室里,找出了《马列著作选读·政治经济学》、《政治经济学教程》等已经发黄的书。这些书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时的教材和读物。
看到这些书,董丰均想起来,那会儿教他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黄思谦教授,似乎也曾对如今张道旭提出的问题有过疑惑。不过,教授在当时只是留给了台下听讲的学生们一个思考题,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。
30岁出头的董丰均当时也没有思考出个所以然。回到郧阳中学的课堂上,这个已经教了8年政治课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:“一切以参考答案为标准,因为高考只认参考答案。”
这种策略收效明显。董丰均所带的高三学生,陆续在高考中出了好几个鄂西北地区的政治单科“状元”,其中一个班的高考综合成绩更是创造了该校历史上“难以逾越的奇迹”。
虽然在备课时会发现有些地方自己想不通,在教高一学生学习、带高三学生复习时,也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,但这位政治老师觉得,让这些山里的娃子们背好参考答案、高考考出高分,才是最大的“政治”。
“所有的不通,也就放下了。”董丰均回忆说。
并且,他当时很真诚地认为,“教材不是一般的书,代表着已经公认的文化、科技和思想成果,代表着国家意志。不仅印量最大,而且通过最正规最有效最强制的渠道,经老师向学生灌输”,“教育部门在编写教材时,肯定是慎之又慎的”。所以,教了27年政治课,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材会有问题。
也是在这不问对错的27年中,董丰均一步步由学校的团委书记、政教处主任、校办主任,最后升任副校长。而他的政治教学水平,也在整个十堰市得到认可,被选为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。
27年下来,董丰均手里的中学政治课本内容和高考重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最初包括“哲学”、“政治经济学”、“科学社会主义”、“社会发展简史”和“时事政治”等5大块的内容。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,“科学社会主义”这一部分被取消,再后来“社会发展简史”被“政治学”所取代。
上世纪80年代,为了让学生了解“时事政治”,董丰均曾把家里好不容易凭票买来的日立牌电视机搬到教室里,让学生们看新闻。他旋转摇晃着天线,尽力让画面变得更清楚,然后自己站在那里扶着天线。
近20年后,董丰均到宜昌旅游时,一位当年的学生动情地向董蕾讲述了这些往事。那个孩子已经上中学的学生说,他还记得有一天雷雨交加,自己一直担心扶着天线的董老师会被雷电击中。
董丰均自己则顾不上担心这些,他当时正被一些问题困扰着。尤其是在“苏东”剧变之后,这种困扰越来越大。“我当时对教材里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,社会主义必然胜利’的说法确实有疑问,怀疑帝国主义到底会不会灭亡啊。”他笑着回忆道。
不过这种困扰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很快,他的这种疑问就出现在了学生的考题里,而从这些考题的参考答案里,董丰均找到了新的理论逻辑,疑问自然也被打消了。
在学校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上,这位旁征博引的主讲老师也变得更加应付自如了。他的讲课风采,折服了不少学生。
“他讲党课,不仅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学识渊博,而且说话很真诚。”目前正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吴胜涛回忆说。他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董老师给自己上党课时的情景。
几节党课之后,当时的高二学生吴胜涛在一天下午放学后,敲门走进了董丰均的办公室。在张口说话之前,吴胜涛先给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,然后说明自己的来意。他刚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,感觉自己的政治课跟不上,很多考题不会做。他听一些毕业学长说,董老师不像有些政治老师,上课只会念课本,而是看马列原著,然后结合课本深入浅出地应用到讲课中。所以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长能给自己补课。
学校里有这样肯学好学的学生,董丰均感到很高兴。他告诉这个怯生生的孩子:“没问题,只要我不开会,你下课后随时可以来找我。”
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,董丰均除了教自己班上那些高一、高二学生的政治课,还在每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之间,义务辅导自己眼中的这个“可造之才”。每当有会议的时候,他会提前告诉吴胜涛,或是在办公室里留张纸条。
最终,吴胜涛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,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。这番师生情,也成为郧阳中学校园内的一段佳话。
看得见的高考,看不见的政治
2002年,吴胜涛大学毕业后,选择到北京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做了政治老师。他坦言,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董老师的影响。
初执教鞭的年轻人,从他的老师那里吸取经验,尽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。在上政治课时,吴胜涛欣喜地发现,“只要不照本宣科,言之有物,学生还是很买账的”。他的努力,也让他在校内教学考评中,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。
然而在备课的时候,吴胜涛常常发现,有很多问题自己想不通,背下来很容易,跟学生讲清楚却很难。
他经常就这些问题跟人讨论,发现不少老师也有同感。但也有人开导这个年轻人:“想那么多干吗?中学政治课,对老师来说,只是一个饭碗;对学生来说,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。”
有时候,吴胜涛会把课本里那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,跟教研员讨论。但他发现,进行一般的探讨还可行,一旦这些问题成为考题,有了参考答案,再要讨论就很难了。
几年的任教经历以及与同行之间的交流,让他越来越觉得,很多老师根本不相信自己所教的东西。“他们觉得政治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,稿子已经写好了,照着念就行。”当然,更让这个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是,不少政治老师不仅不看书,而且认为课本里那些东西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。
没有了“对知识的深信”,这顿时让吴胜涛失去了授业、解惑的快乐。他甚至觉得,政治老师处境尴尬——“官方说政治很重要,实际上,无论是学校、老师还是学生,都没把政治课当回事,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。”
他时常把这种感觉跟董老师交流。但董丰均总是告诫这个曾经的学生,当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。
在湖北省的一次教研会议上,董丰均主动起来发言,话题便是“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”。他的理由很简单:孔子能成为万世师表,不是他语文和数学教得好,也不是他艺术教得好,而是他政治教得好。
但是董丰均也很明白,政治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,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。
有一次,省里一位教研员到十堰市传达中学课程改革的有关精神。在会上,董丰均提出了自己关于政治课教学的一些想法。他说罢,那位教研员随口嘟囔了一句:“政治不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吗?”
更让董丰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,从1993年起,理科高考便不再考政治了。他认为这是“国家政权削弱了对政治课的重视”,因为中学政治基本处于“不考就不学”的状态,而理科学生多,聪明的学生相对也多,这些聪明的大脑大都抛弃了政治课。那些没法抛弃政治课本的文科生,很多人对政治课也提不起兴趣。
董丰均为此忧心忡忡。“政治课除了教娃子们考试,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人生哲学。”他强调道。
但他也不得不承认,更多的时候,政治老师和学生们只是为了考试在学在拼。他们不得不依赖参考答案,进而不得不依赖政治课本。
不知对错的7年
所以当年轻的政治老师张道旭提出疑问时,董丰均意识到,这个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了。
除了翻出自己当年的进修课本,这个在妻子眼里“一辈子爱抬杠,钻牛角尖”的人,还跑到市图书馆借出了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。
在通读这些书籍之后,他写出一篇文章《纸币到底有哪些职能》,认为“教材应做适当修改”。文章后来发表在2004年第8期的《中学政治教学参考》上,他还收到了70元的稿费。
回到课堂上,他手里的教科书并没有如他所愿“做适当修改”。他在论文里所思考的问题,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。
虽然已经认定课本有自相矛盾之处,但董丰均在给学生讲课时,还是紧扣课本,“即使错了也要按照课本来”。
“没办法,娃子们要参加高考,要升学,而高考只认参考答案,参考答案则以课本为标准。”他感慨说。虽然深刻感受到,这种只背标准答案,不问问题的教学与考试,会禁锢创新精神和思想,但他无能为力。
让他感到遗憾的是,在教学过程中,虽然自己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,不主动去讲自己的疑问,但学生也很少提出问题。
董丰均特地将2010年12月24日的《人民日报》第12版收藏起来。因为上面刊有原国家总督学柳斌的文章《当前教育最缺“问”》。文章写道:“我们现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,不是在学‘问’,而是在学‘答’。”董丰均特地将文中类似的语句,用红笔划了出来。这一弊端,他感受颇深。
自己的文章在2004年发表后,董丰均把文章寄给了敢于提问的张道旭,算是老师给学生一个“负责任的回答”。
在思考怎样回答张道旭的过程中,董丰均对货币有了更多的思考。2005年,他写成一篇论文《试析哈耶克<货币的非国家化>的不可行性》,拿到一家期刊发表。由于驳斥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,编辑疑虑重重地问他,“会不会闹笑话?”董丰均告诉对方,“绝对不会,你要相信我。”这篇论文最终发表了。
一年后,他又写出论文《对当代货币的理论阐释》,针对马克思提出的“货币天然是金银”一说,他提出“货币天然是信用”。
因为这篇论文,董丰均在2006年12月收到一所重点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用稿通知。通知说,他的“大作”将会刊载在该刊2007年上半年的“专辑”里,但他需要在收到通知的7天内,交纳版面资助费800元。
得知自己的论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,董丰均喜出望外,随即寄出800元。论文如期刊载在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专辑上,这一度让他认为自己“解决了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”,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。
然而这种快乐在当年暑假就匆匆消失。一位校友回校看望老师,董丰均跟她聊起了当下的社会现象,感到痛心疾首。不知不觉中,他们的话题转到学术腐败上。校友提及,一些学术刊物为了挣钱,常常以出增刊和专辑的形式收取版面费。尤其是“专辑”,印刷后一般只寄给文章作者,而里面的文章,很多在期刊文献的数据库里根本检索不到。
听到这些话时,董丰均想到了自己的文章,虽然尽量不动声色,脸上却是一阵又一阵的滚烫。
回到办公室,他迅速在网上检索,结果真如对方所说。
“我被愚弄了!”董丰均至今仍难以掩饰当时的惊诧与愤怒。
他随即致信该刊编辑部,愿意再出800元钱,要求将论文发表在正刊上。编辑部未予理睬。他再次致函询问,编辑部终于回信说,“董先生在信中所阐述的文章的学术价值,至少本刊相关编辑对此并不认同”,故只能发在注有“专辑”字样的增刊里,“只是普遍地,专辑的订阅量很少”。
“不认同学术价值,但只要给钱就发表,这难道不是惟利是图、不负责任并且学术良心泯灭吗?”董丰均愤怒地说道。
他找到自己在武汉当律师的学生,试图跟编辑部打官司。但学生告诉他,“这种事儿太多,打官司没什么意思”。董丰均只好作罢。
就这篇文章,他还曾在朋友的介绍下,与一位经济学教授取得过联系。
打通电话后,教授上来就问:“你是不是想发表文章提职称?”
董丰均给出了否定的回答。他告诉对方,自己已经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,关心的不是职称,而是自己对政治教材的一些想法。教授听完后,告诉他:“这个问题理论价值不大。”
另一位经济学教授,在某知名大学主办的期刊里担任编辑,是郧阳中学校友。董丰均给他寄去论文后,打电话告之自己的这篇论文“是要纠正政治教材的错误”。
电话那端,教授略有迟疑:“教材,教材?……”董丰均顿时领会到,中学教材里的错误,在教授们看来实在是个小问题。
但在董丰均看来,这不可接受。以他的经历,他知道在教学过程中,中学师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。
“理论界有争议的东西,我们教学中得按教材上讲的处理。教学是为了参加高考,高考得靠正确答案得分。”张道旭说得更直白。
这个当年勇于提问的政治老师坦言,大部分政治老师都是教书匠,对很多问题都没有思考,或者认为没有思考的必要,不会像董校长那样去思考。他介绍说,跟语文、历史等其他学科不同,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,真正教得好的政治老师也很少。有影响的中学政治老师,大都是编高考复习资料,或者是研究高考命题的老师。
这一点也得到郧阳中学政治教研组组长丁仕国的认同。“政治老师确实没有特别有声望的。”他说。
丁仕国介绍,稍微有点名气的政治老师大都热衷于编资料、搞讲座,没人像董丰均这样跟政治教材较真。
2008年,董丰均发现已经使用了3年的高一《思想政治》教材上,有两处表述错误,一处是“纳税人”的定义里掉了一个关键的字,另一处则是将定期储蓄的存期种类搞错了。
发现这些错误后,董丰均及时写了一篇小文章,刊登在当地的一家刊物上。他坚持认为,“教材是最权威的知识载体,不能容许出现可以避免的错误。”
我只是追求真理和思考的权利
2008年,董丰均曾托人将自己的论文发给国内一份权威的经济类期刊。在等待了3个多月之后,他得到的答复是:“因版面紧张,无法刊登。”
这样的拒绝没有让董丰均灰心,反而让他心中有了更多的希望。他认为权威期刊以“版面紧张”而非“没有学术价值”的理由拒绝自己的论文,或许说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非毫无价值。
在几张已经起皱的稿纸上,董丰均将自己收集来的各种正规期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,很详细地记录下来。他先后给这些期刊投稿,最终都换来了同一个杳无音讯的结局。
2009年4月,这篇论文终于在一本名为《现代经济》的刊物上发表。不过,为此董丰均支付了900元的版面费。3个月后,他的另一篇论文在《中国教育发展研究》上发表,花费了他460元。
这期间,在吴胜涛的联系下,北京师范大学的“师范教育·名家讲坛”系列之“光荣的人民教师”讲座,邀请董丰均讲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。组织者误将他介绍为中学特级教师,结果他一上台就纠正,声明自己只是高级教师。
据他的同事介绍,在最有机会晋升为特级教师那年,身为学校领导的董丰均将机会让给了一位普通老师。再后来,评特级教师有了课时量的要求,作为校领导的董丰均因为代课少而失去了机会。
这也难免让外面的人认为,他发表论文是为了评职称。实际上,在2009年秋天被定为正处级调研员后,董丰均应学校的要求,才首次将自己发表论文的情况汇报给学校。
在2009年6月8日的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结束后,57岁的董丰均送走了他所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,也告别了他坚守33年的政治课讲台。被定为调研员后,他可以不用再上课,也不用每天打卡上班。
不用教课,让董丰均的日常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,但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些遗憾。
“把知识讲给学生,让学生理解,看他们会心地笑了,这是一种享受。”董丰均翻着那些自己曾经用过的教科书说道。
说到激动处,董丰均常常会撅着嘴,双目圆睁,满脸通红。他经常跟年轻人说的一句话是:“真理面前,人人平等。”
2009年初冬,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老同学。同学问他在忙什么,他回答在研究货币。对方很意外,他竟会对钱币感兴趣,于是热情地说,自己认识十堰市钱币学会的人,可以介绍他认识。董丰均马上纠正道:“不,我要联系的是金融学会。”
结果,在听了他“货币天然是信用”的提法后,这位曾经担任市社科协领导的同学,直斥董丰均竟然提出跟马克思不同的观点。同学说了一句,“你这叫狗胆包天,无知者无畏”,然后挥手离去。
接下来的冬天,董丰均几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,写出了10余万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,并打算出书。在写作的过程中,他一直充满着自信。因为在他告别讲台之时,拿到的新政治教材上,谈到纸币时已经不再讲纸币没有价值尺度、贮藏手段、世界货币的职能。
书稿完成之后,董丰均几经辗转,通过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联系到一家出版社,出版了这本名为《货币天然是信用》的小册子。他需要为此支付3万元。他的6个学生得知这件事情后,共同捐助了3.1万元。
书出版之后,有毕业生提出要把董丰均手里的几百本书全买了,算是对老师的支持。这遭到了董丰均的拒绝。他的理由很简单:“我不是为了卖钱。”
每次碰到自己认识且觉得有见解的人,他都会主动送给对方一本书。不过送之前,他都会先问一句,“读不读?不读就不送。”送之后,他还会追着问对方读没读、有何感受。
他先后已经送出了几十本书,只有那位说他“狗胆包天”的同学很认真地给他反馈。这多少让董丰均有些失望。
侄女在武汉一所高校经济学系读研究生,董丰均希望侄女的导师能看看他的这本书,评判一下他的研究。但侄女回答:“导师忙得不得了,哪有功夫读你的书!”
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,他特地带着书到一所著名高校,想向该校经济学院院长请教,但刚进学院大门便被保安拦住了。在他说明来意后,保安告诉他,院长“忙得很”。他只好到学校的大门口照了一张相,以证明自己来过。
这一次的遭遇,让董丰均很难受,甚至觉得屈辱。“如果专家们论证我是错的,我认,而别人也就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。但是,你不能认为我是鄂西北小山沟里的一个普通老师,就认为我没有思考的权利,并且对我的观点不闻不问。”
从世博会回来后,董丰均跟随旅游团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。团里只有他一个人专程去了圣十字大教堂。他特地花5欧元买了一张票,在马基雅维利墓和伽利略墓前面,分别照了一张相。“这是个求真的民族。”董丰均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。
这种形势下,政治怎么教?
经常有当中学政治老师的同学、同事、朋友和学生向董丰均诉苦:现在的政治课越来越难教了,学生们对课本越来越不感兴趣。
董丰均则告诉他们:“我们现实的问题,一个是腐败,一个是缺乏民主。政治课本里对这些问题,没正视,没解释,政治课上谁又敢讲呢?学生自然说你空对空。”他认为,政治课在学校里比较尴尬的原因,一是课本与现实脱节,二是政治老师自身素养也有问题。
对此,吴胜涛也深有感触。“政治课上得一直比较拘谨。很多人认为,只要讲的东西和课本上不一样,就是反动的,搞得一些比较好的政治老师也觉得在政治课上‘探讨是没有意义的’。”他说。
最终,当了4年中学政治老师的吴胜涛辞职离开了讲台,因为“满腔热血地干,最后不知道有什么意义,连自己也困惑”。
董丰均则不肯就此放弃,因为有一些经历让他记忆深刻。有些他教了3年的学生毕业后,他问对方:“你说世界上有没有鬼?”学生回答:“有鬼,有鬼。”而当他与一些政治老师聊起这个话题,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。他将这视为政治教育的失败。
“政治课上的道理如果不讲通,那些只知道背答案,然后说自己懂了的人,只能是假懂。”他说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认为政治课本上更不能出现错误。这也是他与政治课本较真儿的原因。他比喻说:“这就好比大庭广众之下,有领导不小心裤子开了一个叉,很多人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提醒他,但我得说出来,不要让他丢人。”末了,他又补上一句,“不然现在这种形势,政治怎么教啊?”
2010年12月31日,董丰均带着他的书和教师资格证到了教育部,想找负责教材编写的有关部门。他在传达室被拦住了。他告诉对方:“教科书很重要,但上面写错了。”对方则回应:“你说错就错啦?”
他没能进去,只能退而求其次,打算在教育部门口留张影。但他刚掏出相机,还没摆好姿势,便被保安喝止:“这里不让照相!”他只好去后门照了张相,然后略带失望地踏上了回十堰的列车。(本报记者 王波)
(责任编辑:孙宾)




发表评论
网友评论
查看所有评论>>